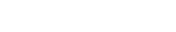如今,太多人想“做”文化,太多的钱想要把文化“产业化”;如果都是真诚的、含着敬畏心和正二八经研究研究的意图的,都没错,都该赞。可如果只是想借这两个字“增色”、“提高档次”,甚至仅仅是把这两个字当作虚幻的光环,实在还是应该多加小心。

(秦始皇焚书坑儒)
(话剧《伏生》,秦博士伏生在“焚书坑儒”时,不惜牺牲亲人的生命保护儒学典籍《尚书》,使其得以留存于世的故事。)
(一)文化一词的由来
“文化”一词,深究起来,大概是由“效仿西学”的时候才开始流行的,继而成了后来被普遍认同并且越捧越高的常用词。
不敢说,这俩字儿,就是从大力主倡“效仿西学”的晚清时期才“诞生”的,没考据。但至少,在那之前,大多数文献中,实在是很难见到。当然,“很难见到”,不能就说成是肯定见不到。“很难见到”的,也仅是“文”字和“化”字组合成词的样子。而“文”和“化”这两个字,分开来,却是古已有之。
(秦始皇下令“焚书坑儒”,伏生传奇般地将儒家大成之作《尚书》以奇特的方式保存下来。)
先不管这两个字怎么就被组合起来了,也暂不去计较最初施行了这个组合的那个或那些人,是基于了怎样的理解、考证、意图。当真纠结起来,不仅很麻烦,而且,也不见得比从“根儿”上读解这两个字,意义更大。
今时,不管什么、谁,都习惯或说时兴拿“文化”二字做标签、封面、噱头,满一副不忌口的豪气和高大上的贵气,全不论合宜与否。
文不对题,或许可忽略不计;尴尬、闹笑话,就多少得在意了,不为自己,也实在该为什么还都不太懂只管吸收的孩子们想想;再要是错谬了、冒犯了、张冠李戴了,就难免老话说的“造孽”之嫌了。
(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佛:击破焚烧佛像及佛经,拆毁寺院,活埋僧侣。)
看的听的多了,就实在有点儿不忍——遇见一个人拿裤带当围脖,可以当没看见;一群人拿裤带当围脖,也大可以笑笑过去罢;可要是大家都跟着学起来,知道一点点端倪的,就实在有提醒一下下的责任了。当然,提醒,不等于就想要改变什么。也许,随着社会的发展,裤带和围脖就不分了呢。提醒,无非是想留下一个声音:那原本是裤带,围脖原本是另外的样子。仅此而已。
好多事儿,只要稍稍深究一下“本源”,就可以明朗不少。真的是!
(二)关于“文化”,暂且从“根子”上“究”上一“究”
任何社会形态,无论是否具备完整的“国家”或者“阶级”的概念,只要达成一定规模和稳定程度的“聚集”,就一定具有“意念”上的共识。